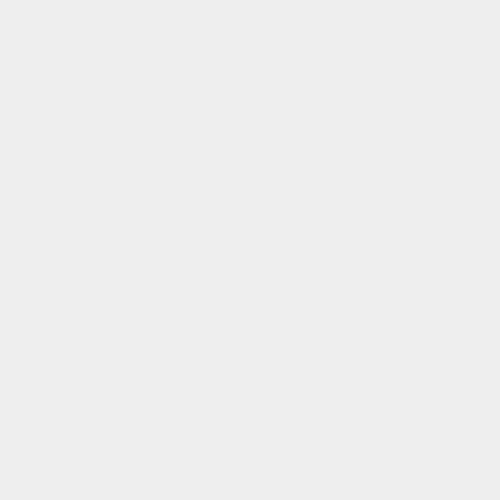八字看哪些人旅游会有好运
八字带驿马,往往热爱旅游,同时容易好运
八字算命太阳运是好运吗
太阳运 因该是用紫微斗数的算法, 值太阳,即是事来发达,要是不带七杀,可白手发至百万富翁。
什么纹身能带来好运?
纹你自己觉得能带给你自己幸运的图案,但是一般还是不建议纹身。 一,纹身(tattoo )也可以写做文身,又叫刺青,是用带有颜色的针刺入皮肤底层而在皮肤上制造一些图案或字眼出来。即指刺破皮肤而在创口敷用颜料使身上带有永久性花纹。 二,在皮肤上造成隆起条纹瘢痕的作法,有时也称为文身。平纹文身在全世界大多数地区均有实行,肤色较深的民族没有这种习惯,中国近几百年间也比较少见。许多民族认为文身可以防病袪灾。 三,纹身不要盖住伤疤。
什么纹身能带来好运?
纹你自己觉得能带给你自己幸运的图案,但是一般还是不建议纹身。 一,纹身(tattoo )也可以写做文身,又叫刺青,是用带有颜色的针刺入皮肤底层而在皮肤上制造一些图案或字眼出来。即指刺破皮肤而在创口敷用颜料使身上带有永久性花纹。 二,在皮肤上造成隆起条纹瘢痕的作法,有时也称为文身。平纹文身在全世界大多数地区均有实行,肤色较深的民族没有这种习惯,中国近几百年间也比较少见。许多民族认为文身可以防病袪灾。 三,纹身不要盖住伤疤。
狗狗名字带来好运
铃铛,铃铛在古意和佛家的寓意就是平安吉祥的意思。
带好运的微信名
心想事成、行好运、……
可以带来好运的游戏名字
带来好运的..我很纠结.. 木有。 你说下喜欢什么风格的。 诗意的 现代的 风雅的 ?
中国现代主义诗歌在中国三十年的历史命运
重建现代诗的起点 要寻找当代诗歌历史变化的某个关键性起点,似乎有若干个标志。最初有人曾以1976年的“天安门诗歌运动”作为一个开端,后来又逐渐意识到,这个时间的起点应在上世纪60年代。但是1978年或许也是一个关键性的节点,因为在这一年中,以一份油印诗刊《今天》的问世为标志,以“潜流”形式存在于地下十数年的“新诗潮”浮出了水面。 我们的眼光还可以放得更远一点,从1917年或者1918年前后至今,新诗刚好经历了90年的时间。而由于社会历史和诗歌自身的变化,这90年刚好又显现为三个“30年”:从1918年到1949年是第一个30年,这个时期虽历经动荡和战乱,新诗却沿着自己的道路和意志由雏形到初步成熟,出现了一批优秀的诗人和经典的诗歌作品,在形式上也达到了相当完备和丰富的程度;第二个30年是从1949年到1978年,这期间由于政治意识形态的强力干预,新诗出现了形式上的封闭和技艺上的偏狭与倒退,除一部分坚持现代性倾向的诗人转入了地下和“潜流”写作之外,主流诗人的写作大都被拘囿于概念化和口号化的藩篱中;第三个30年便是1978年至今,诗歌观念经过持续的调整与对峙,逐步回到现代性的轨道,并且出现了空前的丰富与变异,呈现出形式与路向的开放与多元。 很明显,近30年诗歌似乎“先天”地可以成为一个断代的命题,因为通常意义上30年也可以是一个社会变迁的“拐点”,一个艺术运变和成长的逻辑阶段。不管它是否应和着当代中国的政治变革,从1978年到现在,确实是当代诗歌发生“历史性”变化的一个显性的历史时段。 不过关于起点,我们还是要澄清一个容易混淆的问题——那就是作为一个真正的历史源头,谁是“新诗潮”出现的标志?是1978年前后的开始浮出水面的“朦胧诗”吗?这是一个问题。事实上朦胧诗只是新诗潮巨大的潜流存在的“冰山一角”——仅仅是冰山一角露出了水面。它的源头要早于1978年十多年。具有独立思想、叛逆气质和陌生化艺术追求的诗歌早在上世纪60年代就出现了。1968年食指写出了《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和《相信未来》,更早先的时候他还写下了《鱼儿三部曲》。1968年前“贵州诗人群”中已有人写出了《独唱》、《野兽》,1969年写出了《火神交响诗》系列中的《火炬之歌》,1968年哑默已经写出了《海鸥》、《鸽子》。1971年,插队白洋淀的19岁的知青岳重(根子)写下了即使在今天也足以称得上惊世骇俗的长诗《三月与末日》,这还不说那时北京等城市中,大量处在地下状态的“文学沙龙”中的诗歌写作者。这些作品单就写作的水准、思想的高度与含量看,都不输于10年后诞生的“朦胧诗”。 这就是我们可以把1978年作为一个起点的理由。尽管我们应该避免把社会政治的变化当作考察文学的根本尺度,但这一次的确很难绕开。事实上,不但政治气候对诗歌的变化起了推动影响作用,反过来诗歌和它所承载的思想诉求,也同样潜移默化地影响和推动着政治本身。1978年中国政治的变革,同当时的思想界包括文学与诗歌界活跃的状况之间,既是密切关联的,也是互为因果的。因此,在上世纪80年代有关诗歌的讨论中,人们将“朦胧诗”的诞生当作新诗潮发端的标志是有依据的,尽管这个认识存在着“历史短视”,但从广为传播、影响和推动人们的观念解放、社会进步这一点上,1978年对于当代诗歌确有不可替代和抹杀的意义。只是在这样一个时刻,我们需要更加缅怀那些为了这个时刻付出了久远的努力与探求的人们,那些思想与精神的先驱者,他们所推动的诗歌艺术与思想世界中的“改革开放”,比中国现实政治生活中的“改革开放”要早10年以上,当人们享受今天的写作自由的时候,应该想到筚路蓝缕的他们,为他们颁发一枚最大的勋章。 很显然,一个“近三十年诗歌”的命题,其实就是一个“当代诗歌的历史变革”的命题。在这一点上,它与“新诗潮”的概念在内涵上是一致的,选择尺度和眼光必须要具有这样一种历史感与价值偏向,必须要成为一个展现当代诗歌的“历史变革成果”的载体。它因此不应该是一个杂烩和折中的选本,一个照顾到各个方面的平衡与“撒胡椒粉”式的选本。 分化与多元之路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之交的中国,类似乍暖还寒的早春,政治变革的步伐节奏不断出现令人难以预料的犹豫和变化,在文化上则更有激进力量与保守观念之间的紧张对峙。诗歌在这个时期所置身的环境和所起的作用可谓相当敏感,这是朦胧诗从一开始就处在“风口浪尖”的根本原因。表面上,在关于朦胧诗的讨论中,“崛起论”者并不占上风,1979年到1981年前后的朦胧诗大讨论、1983年末到1984年的“清除精神污染”,都是以崛起论者的沉默或“检讨”来结束的。但在广大的青年读者那里,新的诗歌观念与形式却在短短的几年时间里广为传播,成为了价值共识。到1985年,伴随着政治上改革开放进程的加快,原来严重的诗学对峙突然被搁置了,保守的意识形态代言者的权威地位一下子失效,而由朦胧诗所承载的新的诗歌观念,则悄然成为了事实上的胜利者——似乎不战而胜。这是一个戏剧性的结果,看似紧张压抑、曲折惊险的诗歌变革论争就这样轻易地结束了。然而“戏剧”本身尚未结束,历史又展现出它奇怪的逻辑:作为事实上的胜利者,朦胧诗在紧张与压力之下所拥有的光环也同时消失了,它的意义忽然变得单薄和虚浮起来,朦胧诗人原来几乎作为“文化英雄”的公共形象与自我期许也陡然落空了。用那时的批评家朱大可的一个比喻来说,就是“从绞架到秋千”,环境的变化使“绞架上的英雄”变成了“秋千上的游戏者”,它的意义随着这一身份的转换而迅速弥散和消失。 1986年由徐敬亚等人策划的“中国现代主义诗歌群体大展”,其文化含义与这个时代中国整体的文化状况一样,可谓含混和多义,很难予以清楚的解释。其中当然有作为个体觉醒的先锋精神——有西方20世纪前期的未来主义以及超现实主义等“现代主义”运动的影子(如“莽汉主义”、“大学生诗派”等),有刚刚萌生的消费主义、大众文化、反精英主义新市民思想的胚胎(如“他们”),有与这个时期主流文化合谋的、认同新生活之“合法性”的青年亚文化成分(如这时期流行的“生活流诗”),有少量的对西方结构主义、语言哲学等新思潮的朦胧追比与模拟(如“非非主义”、“新传统主义”等),还有与新的民族主义文化思潮相联系的“寻根”一族(如“整体主义”等)。总之,它们非常敏感地预示了中国从意识形态的一元性社会结构,到结合了市场性因素与大众文化参与的二元性社会结构的转换,这一历史性转折的信息,也使诗歌内部的审美与技术元素得以分化和彰显出来。而原来在与时代保持了紧张关系的格局下,这些内部的问题很难上升到显在层面,这是它的积极意义。但是,在一个公众的自主性文化力量还十分孱弱的时代,这场匆匆忙忙“早产”的诗歌运动,只是承担了一个仪式的作用,并未留下太多有价值的文本。 但是上世纪90年代诗歌的发育却与“第三代”的崛起有关,从这一点上说,他们是属于“先成名、后成长”的幸运的一代。上世纪80年代对主流文化地位的迷恋,对于“参与”社会发展或变革的强烈冲动,在上世纪90年代变成了对公共价值的深度怀疑和对自我价值的深入理解。这时,外部压力的重新出现所导致的逆境性与悲剧性角色,再一次帮助了这些年轻的诗人,促使他们很快建立了自己的“知识分子身份”。可以说,在没有经历这场转折之前,他们还是一批处在青春期的“长满粉刺”(欧阳江河语)的叛逆者,但此时他们却加速了自己的成熟。其次,“圣殿的沉沦”也使一个久违的“江湖世界”(见周伦佑:《第三代诗人》)浮出了水面,这是当代诗歌乃至当代中国文化的一个重要变化。与古代中国社会相似的一个民间江湖世界,正好为失去庙堂的知识分子提供了生存的庇护所,古代的知识分子正是在这个世界中建立了他们的另一套价值系统。而上世纪90年代的中国诗人不但模拟了这一方式,同时也体味到西方式自由知识分子的价值立场,承担起当代性的思考、批判和建构的工作。此外,“专业性”的写作角色,也因为上述身份的确立而得以确认,这大大改变了当代诗人写作的技艺自觉,使得上世纪90年代诗歌在文本建设上取得了意想不到的进步。 事实上,为陈东东、欧阳江河和西川等人所说的“知识分子写作”的概念,应该是在上述意义上理解和建立的,而不是指写作者的“职业身份”——是在学院或研究机构里就职,它应该是一种“精神归属”、“批判角色”和“专业能力”的合称。至于修辞是更像“口语”还是更像“书面语”,并不是根本意义上的分歧。分歧只是表明上世纪90年代诗歌写作中风格与形式的多元化。 1999年的“盘峰诗会”,是上述分歧的集中爆发。在这次会议上,京城和外省的诗人关于诗人的角色、与现实文化中心权力的关系(包括与西方文化权力与诗歌观念之间的关系)、语言与修辞的向度等问题,发生了激烈的论争。一般认为,这场争论除了观念上的分歧之外,很大程度上是第三代内部对于“经典化”程度的某种偏向的争执——居于北京的诗人在国际交流中占得了先机,在上世纪90年代后期他们经过国际汉学界的介绍“出口转内销”,获得了很大名声,而相比之下外省诗人却似乎所获甚少。但这仍然只是一个现象,现在看来,导演这场纷争的,除了一些具体利益因素之外,宏观上其实是根源于“全球化”这根魔棒的作用。上世纪90年代前期中国相对封闭的状态下,诗人与文本的意义是在单一坐标与尺度上建立的,压力远大于利益,所以并不存在重大分歧的可能,甚至1995年前后的“人文精神讨论”,诗歌界也很奇怪地并未卷入,而这已经是一场明显的价值分裂了——面对市场经济带来的价值转换、其与人文精神之间天然的分离关系,知识分子应该如何持守自己的文化角色与价值立场?诗歌界似乎尚未表现出应有的敏感。然而到上世纪90年代后期,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和文化交往的日益增多,“全球化”的脚步忽然之间变得如此临近,国家在经济领域对这一进程的积极推进,当然也影响到文化领域,诗人同全球化的文化趋势与价值尺度之间的关系,陡然变得复杂起来。是彻底融入西方知识分子的精神趋向,还是偏重于保守中国本土的文化价值,再次变成了一个难以解答和难以判明的问题。 随着这场分歧的出现,代表了更年轻一代审美取向与文化观念的“70后”、“80后”诗人也迅速登上了历史舞台。从上世纪60年代诗人中又分化出了“第三条道路写作”,特别是随着网络新媒体的迅速扩张,诗歌借助网络环境带来的新的伦理与美学情境、借助上世纪末与本世纪初的“狂欢”氛围,迅速形成了一个纷繁多样、旗帜林立、中心消解、众声喧闹的局面。一个现实与虚拟双重意义上的“新江湖世界”,重新成为如今诗歌写作的广阔背景和舞台。这样一个变化,如果就其历史的意义来看,不亚于1990年前新诗从旧诗中脱胎的骤变,因为网络传播环境彻底改变了诗歌写作的主客体情境,改变了传播方式,修改了诗人的主体身份与自我想象,改变了写作的伦理与修辞方式,所以原有的许多价值规则都要面临失效和调整。但这种变化绝不是“进化论式”的逻辑,从精神的意义上诗歌所面临的考验和机遇一样多,而从文本的意义上,这场变化的正面意义还远未得到充分证实。 诗歌 让我们收获了什么 30年我们收获了什么?读者会问这样特别直接的问题。这个问题说来也容易,因为我们毕竟收获了很多,但要说清说透,似乎也很难。 我们找回并且确认了“诗歌的精神”——我以为这就是“近三十年诗歌”最大的收获。什么是诗歌的精神?要素当然很多,但最重要的应该是自由的、独立的、人文的和艺术的精神,是诗人以自主的意志对历史、社会、时代和现实以及一切精神领域的直接面对,这当然也是诗歌的基本要义,但是它在很长时间里却因为种种外部原因而被压抑乃至丧失。在上世纪60年代到上世纪70年代,它虽然在少数诗人那里得以存在,但却并没有合法性,而在上世纪80年代以后它的合法性的获得也仍然经过了漫长的求索过程。时至今日我们则可以说,诗歌已经获得了这样的权益和能力,它所涉及的范围和深度——从无意识世界、人性本能到人文主义精神,到一切文化传统,到对现实予以把握的各个领域,都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自主性与自由度。诗人靠自己的努力拓展了诗歌的疆界,将精神的触须伸张到了一切应该抵达的领域,这就是诗歌自由精神与意志的实现。对于这一点,没有历史感的人很容易会不以为然,但对于一切未丧失记忆的人来说,对其间所包含的挫折与艰险、成功与欣悦,一定会感慨万千。 诗歌因此也回应了它的时代,这个历程中的文本记录下了它的精神轨迹,也勾勒出了一部当代中国的精神历史:在与30年社会政治改革一样不平凡的风雨历程中,在上世纪80年代初期的乍暖还寒里,在上世纪90年代初的灰色记忆中,在市场与物化时代的逼挤与诱惑中,还有在这一环境中的个体沉沦与底层困顿中……当代诗歌的写作者们,历经磨难和曲折,留下了他们真实和足以与这些曲折磨难“相对称”的精神足迹。 再一点是诗歌“经验的宽度”,这可以说是一个时代的诗歌是否成熟和繁盛的标志。什么是经验的宽度?它是指一个时代的诗人感知世界的精神界面,把握物化世界与主体世界方式的丰富程度,这必须是足够宽阔、足够多元的一个界面,它应该无孔不入、无所不在。换句话说,诗歌应该变形为一切,一切皆有诗歌的可能。很显然,这是诗歌“现代性”特质的一个标志和条件。因为单纯古典意义上的“审美”,在现代诗歌中必须转换为一种“深度经验的表达”,才能支持诗歌本身的意义深度与文学性价值。在这一点上,我以为当代诗歌获得了足够空间。有人叹息如今的诗歌已经“失去了标准”,但不要忘了,它的另一面就是多元的伦理尺度和无限的可能空间。曾几何时,人们把描写个体的心理活动,展现一丝细小的“心灵曲线”(徐敬亚语),都视作是晦涩朦胧和不健康的情调。而今,连本能与无意识世界的微小而敏感的震颤,甚至不那么“高尚”也不那么“健康”的震颤,也可以成为一首好诗或“有意味的诗”的内涵。而今“70后”的很多诗人,几乎都是在无意识和“下意识”活动的层面上建立其诗歌写作的“意义”的。这样的写作,在诗歌中也同样成为支持其审美价值与精神深度的有效途径。还有,曾几何时,“形式”也仅仅是被理解为“古典”或者“民歌”的韵律与语言体式,而今连一种纯粹的修辞冲动、一种对形式的试验意趣,都可以堂而皇之地单独支持并确立一个文本。类似陈东东的《雨中的马》、《现实主义者爱箫》那样的作品,几乎只是一个将具体经验掏空之后的修辞外壳,但它也仍然能够灵敏地接通人的细微的无意识活动,并成为一个生动可感的意义媒介,这就是形式与经验的完美结合——当然这也有赖于高水准读者的理解力作为支撑。 第三是“复杂完备的技艺”。这一点尤难说清楚,但也最明显,如今一个稍微训练有素的写作者,单就其作品的技术含量来看,也要远超过上世纪80年代初期大名鼎鼎的诗人。这当然不是一个“进化论”的简单命题,但是作为一种技艺,当代的写作者意识到了它的专业性与复杂性,并且能够以“职业写作”的心态,而不仅仅是以“文化英雄”或者其他角色来进入诗歌中去。这个意识自觉源自上世纪90年代,欧阳江河在《’89后国内诗歌写作》一文中对此已有十分明确的阐释。虽然我个人并不认同离开诗人的襟怀气质、生命人格实践,“技艺”会单独具有意义,但在具备了这个前提的情况下,我同样认为技艺是最终决定文本品质的“唯一”要素。这里我不想就具体的技艺要素进行分析,因为如果不是以个体为研究对象的话,这种分析很难展开。而且,我对于许多人都已谈过的“叙事性”、“修辞”或“形式试验”等问题也无须再饶舌,我只是想说,从现代诗所应具备的要素看,如今的诗歌写作可以说是极其多样和完备的,在意义建立、意象、修辞、细节、结构、节奏、色彩、悖谬关系、戏剧元素、跳转或连绵、暗喻或反讽……所有层面及其综合关系上,都可以举出手艺精湛的例证,与当年朦胧诗人靠使用“警言绝句”或“意象中心”来呈现意义的手段相比,如今的诗人可以说是“武装到了牙齿”。 30年中我们收获了什么?我无意在这里为当代诗歌、为整个新诗作什么辩护,但我坚信这些文本有经得起检验之处——无论是就其思想价值、时代意义、其形式的成长而言,还是就感人的程度与精神含量而言。在重大的历史关节之处,在诸多需要留下痕迹的地方,当代诗人没有缺席。相信再过上若干年,人们对这类问题会看得更加清楚些,尽管他们不会是历史上最好的,但一定是认真思考和回应了自己时代的诗人。 危机 在于衰弱的人格力量 当时常听到有人对诗歌表示失望或者悲观的言谈时,我不免要思考其中的原因。作为一个心中装有文本的读者,我当然不同意他们的类似结论,但必须思考这其中的缘由。为什么我们的诗歌取得了如此多“进步”,却反而愈来愈受到质疑甚至贬损?很明显,要么是他们的“趣味陈旧”,不能跟上诗歌的变化节奏,要么是好的诗歌作品未能进入到他们的阅读视野。前者看起来是一个解释的理由,但从根本上说,我们不能“要求”读者跟上诗歌“进步”的节奏——除非你用作品来吸引人,谁也没有权力规定读者的趣味。古典诗歌拥有的读者从来都是心甘情愿的,为什么现代诗就要求读者要“更新观念”或“增加修养”呢?从后者看,也许是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诗歌“经典化的程度”不够。而这其中也有两个原因,要么是作品本身通向经典的条件不具备,要么是专业介绍、批评家的工作做得不够,但这些其实也微乎其微。因为对于许多爱诗的人来说,他们并不存在“拒绝阅读”的问题,但他们为什么也对诗歌表示了不满? 真正的原因,在我看来是“诗人出了问题”。尽管技艺与文本成长日益复杂了,但诗人的人格精神、人格力量却日渐萎缩了。这是使得诗歌在读者心目中、在社会公共形象中不升反降的根本缘由。很简单,在所有文类中,只有诗歌是最为特殊的。它要求诗人的人格力量与诗歌的文本力量必须通过互相见证而统一起来——就像屈原、李白、杜甫、辛弃疾、苏轼、曹雪芹一样,他们的人生与诗歌写作是互相见证和互相完成的,他们的人生实践、人格力量本身就是一部史诗传奇,而他们的诗歌本身又记录着他们非凡或不朽的生命历程。他们是用非凡的或感人的、令人景仰的或让人悲悯的生命,谱写了不朽的诗篇,他们不但是杰出的诗人,也是人格的楷模……而这样的诗歌魅力、质地与境界,必然是用人格力量建立起来的,读者自然无法拒绝。而当代的诗歌之所以被各种舆论贬损质疑,根本原因就在于人格与写作的分离,他们的职业化或专业化的写作已达到了很高的境地,但“写作者主体”却并未得到有效的建立。 这个问题几乎是致命的,它的复杂不是几句话可以说清的。但是我必须要说的一点是,一个民族的成长,一个文化的确立,同它的诗歌形象的确立是一样的,伟大人格与精神形象的诞生既是结果,又是标志,还是先决前提。当代诗歌文本的成长与诗人人格的成长之间,显然是一个不对称的甚至是相悖的关系。当然我们也曾出现了海子这样用生命承担诗歌的诗人,出现了食指这样用诗歌见证命运的诗人,但总体上他们要支撑起当代诗歌的巨大体积和气脉,还是显得过于势单力孤了。而像顾城这样的悲剧诗人,甚至损毁了朦胧诗人曾经在人们心目中树立的抗争与承担的道德形象,使诗人蒙羞为罪犯的同义语。上世纪90年代的新一代诗人似乎曾经有过不错的机遇,但环境压力的迅速瓦解,也瓦解了他们本来就并不强健的人格形象。我们最终并没有诞生出俄罗斯和苏联时代那样的文本杰出又无愧民族精神化身的诗人。随着市场时代物化力量的介入,传统意义上的人格建立则更成为了被谐谑和嘲笑的对象。这就是上世纪90年代以来技艺与文本变得愈来愈膨胀而精神力量与精神形象却越来越孱弱的真正原因。这是我们都应该思考和警觉的。某种意义上,它也呈现了一个民族整体的精神与文化危机,这是在今天回顾30年诗歌最应深思的问题。
梦到三十年的初恋是啥意思
当你失落、悲伤的时候,最好学会遗忘。不要在乎脚下的路,前面的风光更迷人。过去的就过去了,但是留下的是最美好的回忆,为什么要刻意去忘记呢.虽然不能和他在一起但是,你们有着美好的回忆,我相信他也会把你们美好的回忆永远留在心中的,爱一个人就是要他幸福,要他开心,但是他幸福的前提是你幸福吗,你开心吗,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幸福与不幸福都在自己的心里,等到时间慢慢的过去了,你找到了你的另一半的时候,你就会把你们的回忆放在心底,把你的祝福也同样用回忆带给他,过去的就让他过去,短暂的心痛是难免的,但是不要让自己刻意的忘记什么,那样会更痛苦,只要自己认为自己是幸福的那自己永远都是幸福的.
三十年的朋友建立一个群,请问起一个什么名字好?
友谊天长地久 一生知己 光辉岁月